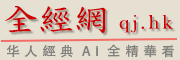晉文王功德盛大,坐席嚴敬,擬於王者。唯阮籍在坐,箕踞嘯歌,酣放自若。
晉文王司馬昭功勳卓著,恩德深厚,座上客人在他麵前都很嚴肅莊重,把他比擬為王。隻有阮籍伸開兩腿坐著,吹哨唱歌,痛飲放縱,不改常態。
王戎弱冠詣阮籍,時劉公榮在坐。阮謂王曰:“偶有二鬥美酒,當與君共飲。彼公榮者,無預焉。”二人交觴酬酢,公榮遂不得一杯。而言語談戲,三人無異。或有問之者,阮答曰:“勝公榮者,不得不與飲酒;不如公榮者,不可不與飲酒;唯公榮,可不與飲酒。”
王戎青年時代去拜訪阮籍,這時劉公榮也在座,阮籍對王戎說:“碰巧有兩鬥好酒,該和您一起喝,那個公榮不要參加進來。”兩人頻頻舉杯,互相敬酒,劉公榮始終得不到一杯;可是三個人言談耍笑,和平常一樣。有人問阮籍為什麼這樣做,阮籍回答說:“勝過公榮的人,我不能不和他一起喝酒;比不上公榮的人,又不可不和他一起喝酒;隻有公榮這個人,可以不和他一起喝酒。”
鍾士季精有才理,先不識嵇康。鍾要於時賢俊之士,俱往尋康。康方大樹下鍛,向子期為佐鼓排。康揚槌不輟,傍若無人,移時不交一言。鍾起去,康曰:“何所聞而來?何所見而去?”鍾曰:“聞所聞而來,見所見而去。”
鍾士季精明且才思敏捷,先前不認識嵇康;他邀請當時一些才德出眾人士一起去尋訪嵇康。碰上嵇康正在大樹下打鐵,向子期正在打下手幫他拉風箱。嵇康繼續揮動鐵槌,旁若無人一直沒有停下,過了好久也不和鍾士季說一句話。鍾士季起身要走,嵇康才問他:“聽到了什麼才來的?看到了什麼才走的?”鍾士季說:“聽到了所聽到的才來,看到了所看到的才走。”
嵇康與呂安善,每一相思,千裏命駕。安後來,值康不在,喜出戶延之,不入。題門上作“鳳”字而去。喜不覺,猶以為欣,故作。“鳳”字,凡鳥也。
嵇康和呂安關係很好,每當想念對方的時候,即使相隔千裏,也會立刻動身去見對方。後來有一次,呂安來看嵇康,正碰上嵇康不在家,嵇喜出門來邀請他進去,呂安不肯,隻在門上題了個“鳳”字就走了。嵇喜沒有醒悟過來,還因此感到高興。所以寫個鳳字,是因為它分開來就成了凡鳥。
陸士衡初入洛,谘張公所宜詣;劉道真是其一。陸既往,劉尚在哀製中。性嗜酒,禮畢,初無他言,唯問:“東吳有長柄壺盧,卿得種來不?”陸兄弟殊失望,乃悔往。
陸士衡初到京都洛陽,向張華詢問應該去拜訪哪些人,張華提出劉寶是其中一位。陸機前去拜訪時,劉道真還在守孝,他生性喜歡喝酒;行過見麵禮,並沒有談別的話,隻是問:“東吳有一種長柄葫蘆,你帶來種子沒有?”陸家兄弟倆特別失望,後悔不該去這一趟。
王平子出為荊州,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。時庭中有大樹,上有鵲巢。平子脫衣巾,徑上樹取鵲子。涼衣拘閡樹枝,便複脫去。得鵲子還,下弄,神色自若,傍若無人。高坐道人於丞相坐,恒偃臥其側。見卞令,肅然改容雲:“彼是禮法人。”
王平子要外調任荊州刺史,太尉王衍和當代名流全都來送行。當時院子裏有棵大樹,樹上有個喜鵲窩。王平子脫去上衣和頭巾,幹脆爬上樹去掏小喜鵲,汗衫掛住樹枝,就再脫掉。掏到了小鵲,又下樹來繼續玩弄,神態自若,旁若無人。高坐和尚在丞相王導家做客,常常是仰臥在王導身旁。見到尚書令卞壼,就馬上神態恭敬端莊,說道:“他是講究禮法的人。”
桓宣武作徐州,時謝奕為晉陵。先粗經虛懷,而乃無異常。及桓還荊州,將西之間,意氣甚篤,奕弗之疑。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。每曰:“桓荊州用意殊異,必與晉陵俱西矣!”俄而引奕為司馬。奕既上,猶推布衣交。在溫坐,岸幘嘯詠,無異常日。宣武每曰:“我方外司馬。”遂因酒,轉無朝夕禮。桓舍入內,奕輒複隨去。後至奕醉,溫往主許避之。主曰:“君無狂司馬,我何由得相見?”
桓溫任徐州刺史,這時謝奕任揚州晉陵郡太守,起初兩人在交往中略為留意謙虛退讓,而沒有不同尋常的交情。到桓溫調任荊州刺史,將要西去赴任之際,桓溫對謝奕的情意就特別深厚了,謝奕對此也沒有什麼猜測。隻有謝虎子的妻子王氏領會了桓溫的意圖,常常說:“桓荊州用意很特別,一定要和晉陵一起西行了。”不久就任用謝奕做司馬。謝奕到荊州以後,還很看重和桓溫的老交情,到桓溫那裏作客,頭巾戴得很隨便,長嘯吟唱,和往常沒有什麼不同。桓溫常說:“是我的世外司馬。”謝奕終於因為好喝酒,越發違反晉見上級的禮節。桓溫如果丟下他走進內室,謝奕總是又跟進去。後來一到謝奕喝醉時,桓溫就到公主那裏去躲開他。公主說:“您如果沒有一個放蕩的司馬,我怎麼能見到您呢!”
謝萬在兄前,欲起索便器。於時阮思曠在坐曰:“新出門戶,篤而無禮。”
謝萬在兄長麵前,想起身找便壺。當時阮思曠在座,說:“新興的門第,真是粗率無禮。”
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,嚐箸白綸巾,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,直言曰:“人言君侯癡,君侯信自癡。”藍田曰:“非無此論,但晚令耳。”
謝萬是王述的女婿。他曾經戴著白色的頭巾,坐著轎子到揚州刺史的衙署。見了王述後,直接對他說:“別人說你癡傻,你確實是癡傻。”王述說道:“並非沒有這種說法,不過後來我就變得聰明了。”
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,桓問曰:“卿何署?”答曰:“不知何署,時見牽馬來,似是馬曹。”桓又問:“官有幾馬?”答曰:“不問馬,何由知其數?”又問:“馬比死多少?”答曰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
王徽之任車騎將軍桓衝的騎兵參軍。一次桓衝問他:“你在哪個官署辦公?”他回答說:“不知是什麼官署,隻是常常看見有人牽馬進來,好像是馬曹吧。”桓衝又問:“那你知道官府裏有多少馬嗎?”他回答說:“我不過問馬,怎麼知道馬的數引”桓衝又問:“那近來馬死了多少?”他回答說:“活著的還不知道,哪能知道死的!”
謝公嚐與謝萬共出西,過吳郡。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,太傅雲:“恐伊不必酬汝,意不足爾!”萬猶苦要,太傅堅不回,萬乃獨往。坐少時,王便入門內,謝殊有欣色,以為厚待已。良久,乃沐頭散發而出,亦不坐,仍據胡床,在中庭曬頭,神氣傲邁,了無相酬對意。謝於是乃還。未至船,逆呼太傅。安曰:“阿螭不作爾!”
謝安曾經和謝萬一起坐船到京都去,過吳郡時,謝萬想和謝安一起到王恬那裏,太傅謝安說:“恐怕他不一定理睬你,我看不值得去拜訪他。”謝萬還是極力邀哥哥一起去,謝安堅決不改變主意,謝萬隻好一個人去。到王恬家坐了一會兒,王恬就進裏麵去了,謝萬顯得非常高興,以為會優禮相待。過了很久,王恬竟洗完頭披著頭發出來,也不陪客人坐,就坐在馬紮兒上,在院子裏曬頭發,神情傲慢而放縱,一點也沒有應酬客人的意思。謝萬於是隻好回去,還沒有回到船上,先就大聲喊他哥哥。謝安說:“阿螭不會做作啊。”
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。桓謂王曰:“卿在府久,比當相料理。”初不答,直高視,以手版拄頰雲:“西山朝來,致有爽氣。”
王徽之任車騎將軍桓衝的參軍。桓衝對他說:“你到府中已經很久了,近日內應該處理政務了。”王徽之並沒有回答,隻是看著遠處,用手板支著腮幫子說:“西山早晨很有一股清爽的空氣呀。”
謝萬北征,常以嘯詠自高,未嚐撫慰眾士。謝公甚器愛萬,而審其必敗,乃俱行。從容謂萬曰:“汝為元帥,宜數喚諸將宴會,以說眾心。”萬從之。因召集諸將,都無所說,直以如意指四坐雲:“諸君皆是勁卒。”諸將甚忿恨之。謝公欲深箸恩信,自隊主將帥以下,無不身造,厚相遜謝。及萬事敗,軍中因欲除之。複雲:“當為隱士。”故幸而得免。
謝萬北伐的時候,常常以長嘯歌詠來表示自己清正嚴明,從來不去安撫和慰問手下的將士。謝安非常喜歡和欣賞謝萬,卻料定他一定會失敗,就和他一同出征。謝安從容不迫地對謝萬說:“你身為主帥,應該常常請將領們來宴飲、聚會,以此來籠絡大家的心。”謝萬答應了,就召集眾將領來,可是並沒有多說什麼,隻是拿如意指著滿座的人說:“你們都是很精壯的士兵。”所有的將領聽了更加怨恨他了。謝安對眾將領多施恩惠以籠絡人心,不管是多大的將領,他都親自登門拜訪,非常真誠地表示歉意。到謝萬北伐失敗後,軍隊內部將士們想要找機會殺掉謝萬,後來又說:“應該為隱士謝安考慮一下。”所以謝萬能僥幸地免掉一死。
王子敬兄弟見郗公,躡履問訊,甚修外生禮。及嘉賓死,皆箸高屐,儀容輕慢。命坐,皆雲“有事,不暇坐。”既去,郗公慨然曰:“使嘉賓不死,鼠輩敢爾!”
王子敬兄弟去見郗愔,都要穿好鞋子去問候,很遵守外甥的禮節。到郗嘉賓死後,去見郗愔時都穿著高底木板鞋,態度輕慢。郗惜叫他們坐,都說:“有事,沒時間坐。”他們走後,都情感慨地說:“如果嘉賓不死,鼠輩敢這樣!”
王子猷嚐行過吳中,見一士大夫家,極有好竹。主已知子猷當往,乃灑埽施設,在聽事坐相待。王肩輿徑造竹下,諷嘯良久。主已失望,猶冀還當通,遂直欲出門。主人大不堪,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。王更以此賞主人,乃留坐,盡歡而去。
王徽之到外地去,途中經過吳中,他知道附近的一個士大夫家有個很好的竹園。竹園主人也已經知道王徽之會來,就命人好好地灑掃園子,並準備設宴款待,在正廳裏坐著等他。王徽之卻坐著轎子直接來到竹園裏,諷誦長嘯了很久,主人已經很失望了,還希望他會來和自己打個招呼,可是他竟然直接出門就走。主人實在忍受不了,就叫手下的人去關了大門,不讓他出去。王徽之因此賞識主人,就留步坐下,盡情歡樂了一番才走。
王子敬自會稽經吳,聞顧辟疆有名園。先不識主人,徑往其家,值顧方集賓友酣燕。而王遊曆既畢,指麾好惡,傍若無人。顧勃然不堪曰:“傲主人,非禮也;以貴驕人,非道也。失此二者,不足齒人,傖耳!”便驅其左右出門。王獨在輿上回轉,顧望左右移時不至,然後令送箸門外,怡然不屑。
王獻之從會稽郡經過吳郡,聽說顧辟疆有個名園,原先並不認識這個名園的主人,但還是徑直到人家府上去。碰上顧辟疆正和賓客朋友設宴暢飲,王獻之觀賞完整個花園後,隻在那裏指點評論優劣,旁若無人。顧辟疆臉色大變,非常生氣,忍受不住說道:“對主人傲慢,這是失禮;靠地位高貴來做視別人,這是無理。失去了這兩方麵,這種人是不值得一提的傖父罷了!”就把他的隨從趕出門去。王獻之獨自坐在轎子裏,左顧右盼,隨從很久也不來。然後顧辟疆叫人把他送到門外,對他但然自若,置之不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