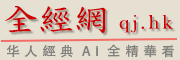劉毅,字仲雄,東萊掖人。漢城陽景王章之後。父喈,丞相屬。毅幼有孝行,少厲清節,然好臧否人物,王公貴人望風憚之。僑居平陽,太守杜恕請為功曹,沙汰郡吏百餘人,三魏稱焉。為之語曰:“但聞劉功曹,不聞杜府君。”魏末,本郡察孝廉,辟司隸都官從事,京邑肅然。毅將彈河南尹,司隸不許,曰:“攫獸之犬,鼷鼠蹈其背。”毅曰:“既能攫獸,又能殺鼠,何損於犬!”投傳而去。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,曰:“毅方正亮直,介然不群,言不苟合,行不苟容。往日僑仕平陽,為郡股肱,正色立朝,舉綱引墨,硃紫有分,《鄭》、《衛》不雜,孝弟著於邦族,忠貞效於三魏。昔孫陽取騏驥於吳阪,秦穆拔百裏於商旅。毅未遇知己,無所自呈。前已口白,謹複申請。”太常鄭袤舉博士,文帝辟為相國掾,辭疾,積年不就。時人謂毅忠於魏氏,而帝怒其顧望,將加重辟。毅懼,應命,轉主薄。
劉毅字仲雄,是東萊掖人。漢城陽景王劉章的後代。父親劉喈,丞相屬。劉毅年幼孝順,年少時磨煉高潔的節操,但喜歡評論人物,王公貴人望風而懼。奇居於陽,太守杜恕請他任功曹,淘汰郡吏百餘人,被三魏之人所稱道。評論他說:“衹聞劉功曹,不聞杜府君。”魏末,本郡推薦孝廉,征用為司隸都官從事,京城秩序井然。劉毅將要彈劾河南尹,司隸不同意,說:“狗去撲獸,鼷鼠蹬其背。”劉毅說:“既能捕獸,又能殺鼠,何損於狗!”扔下證件而去。同郡王基把劉毅推薦給公府,說:“劉毅正直誠實,超凡脫俗,言行不迎合對方。以前為官平陽,為郡之要員,在公府端莊嚴肅,條理分明,朱紫有別,《鄭》《衛》不亂,以孝悌聞名於州郡,因忠貞在三魏被仿效。過去孫陽在吳阪得到駿馬,秦穆公在商人中啟用百裏奚。劉毅未遇知己,沒有自薦。前麵已經口頭講過,小心地再次申請。”太常鄭袤推舉其為博士,文帝征用為相國掾,以病推辭,多年不做官。人們說劉毅忠於魏氏,而皇帝恨他留戀舊朝,將處以極刑。劉毅害怕,應召,改任主簿。
武帝受禪,為尚書郎、駙馬都尉,遷散騎常侍、國子祭酒。帝以毅忠蹇正直,使掌諫官。轉城門校尉,遷太仆,拜尚書,坐事免官。鹹寧初,複為散騎常侍、博士祭酒。轉司隸校尉,糾正豪右,京師肅然。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眾,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、蓋寬饒。皇太子朝,鼓吹將入東掖門,毅以為不敬,止之於門外,奏劾保傅以下。詔赦之,然後得入。
武帝接受禪讓為帝,以劉毅為尚書郎、駙馬都尉,升任散騎常侍、國子祭酒。武帝認為劉毅忠誠正直,讓他掌管諫官。改任城門校尉,升任太仆,拜任尚書,因事獲罪被免官。鹹寧初年,再為散騎常侍、博士祭酒。改任司隸校尉,糾舉豪族,京師秩序井然。官員見勢放下官印的很多,人們把他比作諸葛豐、蓋寬饒。皇太子入朝,樂隊將入東掖門,劉毅認為不嚴肅,把他們擋在門外,上奏彈劾太子保傅以下官員。詔令赦免他們,然後得以進入。
帝嚐南郊,禮畢,喟然問毅曰:“卿以朕方漢何帝也?”對曰:“可方桓、靈。”帝曰:“吾雖德不及古人,猶克己為政。又平吳會,混一天下。方之桓、靈,其已甚乎!”對曰:“桓、靈賣官,錢入官庫;陛下賣官,錢入私門。以此言之,殆不如也。”帝大笑曰:“桓靈之世,不聞此言。今有直臣,故不同也。”散騎常侍鄒湛進曰:“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,人心猶不多同。昔馮唐答文帝,雲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,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。然以此相校,聖德乃過之矣。”帝曰:“我平天下而不封禪,焚雉頭裘,行布衣禮,卿初無言。今於小事,何見褒之甚?”湛曰:“臣聞猛獸在田,荷戈而出,凡人能之。蜂蠆作於懷袖,勇夫為之驚駭,出於意外故也。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,言語有自然之逆順。向劉毅始言,臣等莫不變色。陛下發不世之詔,出思慮之表,臣之喜慶,不亦宜乎!”
皇帝曾到南郊祭天,禮儀完畢,對劉毅歎息道:“你把我比作漢朝的哪位皇帝?”劉毅答:“可比桓帝、靈帝。”皇帝說:“我雖德不及古人,依然克己為政。又平定吳會,統一天下。把我比作桓、靈二帝不是太過分了嗎!”劉毅答:“二帝賣官,錢入官庫;陛下賣官,錢入私門。就此而言,還不如他們呢。”皇帝大笑說:“桓、靈之時,不聞此言。今有直臣,所以不同。”散騎常侍鄒湛進諫說:“人們把陛下比作漢文帝,仍多有異議。從前馮唐回答文帝,說不能用廉頗、李牧而文帝發怒,今劉毅冒犯陛下而陛下歡喜。以此相比較,聖德卻超過他了。”皇帝說:“我平定天下而不封揮,焚雉頭裘,行布衣禮,你當初不說。今天在小事上,為何過分褒獎?”鄒湛說:“猛獸在田,操戈而出,人人都能做到。蜂蔓在懷抱中出現,勇夫為之驚駭,這是出於意外的緣故。君尊臣卑理所當然,說話亦當如此。劉毅開始說時,臣等沒有不變色的。陛下發布罕有的韶令,出乎意料之外,我們高興,不也是可以的嗎廠
在職六年,遷尚書左仆射。時龍見武庫井中,帝親觀之,有喜色。百官將賀,毅獨表曰:“昔龍降鄭時門之外,子產不賀。龍降夏庭,沫流不禁,卜藏其漦,至周幽王,禍釁乃發。《易》稱‘潛龍勿用,陽在下也。’證據舊典,無賀龍之禮。”詔報曰:“正德未修,誠未有以膺受嘉祥。省來示,以為瞿然。賀慶之事,宜詳依典義,動靜數示。”尚書郎劉漢等議,以為:“龍體既蒼,雜以素文,意者大晉之行,戢武興文之應也。而毅乃引衰世妖異,以疑今之吉祥。又以龍在井為潛,皆失其意。潛之為言,隱而不見。今龍彩質明煥,示人以物,非潛之謂也。毅應推處。”詔不聽。後陰氣解而複合,毅上言:“必有阿黨之臣,奸以事君者,當誅而不誅故也。
在任六年,升任尚書左仆射。當時龍出現在武庫井中,皇帝親自去看,麵有喜色。百官將去道賀,劉毅獨自上奏說:“過去龍降在鄭國時門之外,子產不賀。龍降在夏朝的庭院中,涎沫不止,算卦說把它藏起來。到周幽王,災難發生。《易經》說‘龍潛伏不作施展,是因為陽氣低沉’。考之舊典,無賀龍之禮。”詔書回覆說:“正德不修,的確不能接受吉祥。看到你的上表,感到惶恐。慶賀之事,應該慎重地根據禮典行動。”尚書郎劉漢等認為:“龍呈青色,夾有白色花紋,這是大晉偃武修文之兆。而劉毅卻用衰世妖孽來懷疑當今吉祥。又認為龍在井中是潛龍,都不正確。潛即隱而不見。現在龍色彩鮮豔,示人以形,並不是潛。型塹應推究處理。”韶不準。後來陰氣散而又合,璽隧上言:“肯定是結黨營私之臣,狡詐以侍君,當殺而沒殺的緣故。”
毅以魏立九品,權時之製,未見得人,而有八損,乃上疏曰:
劉毅認為魏建立九品中正製,是權宜之製,沒有選到人才,而有八害,於是上疏說:我聽說:執政者,以量才授官為本,此事有三難,但關係到國家的盛衰興亡。人物難知,這是一;愛憎難防,這是二;真偽難辨,這是三。如今設立中正,評定九品,高低隨意,榮辱在手。有皇帝的威福和朝廷的權勢。愛憎和虛實全在於己,對公不負考核之責,對私不怕告發。用盡心計,鑽營各方。廉潔謙讓的風氣消失了,得過且過的習俗形成了。天下紛亂,衹爭品級和官位,沒聽說謙讓,我為聖朝感到羞恥。
臣聞:立政者,以官才為本,官才有三難,而興替之所由也。人物難知,一也;愛憎難防,二也;情偽難明,三也。今立中正,定九品,高下任意,榮辱在手。操人主之威福,奪天朝之權勢。愛憎決於心,情偽由於己。公無考校之負,私無告訐之忌。用心百態,求者萬端。廉讓之風滅,苟且之欲成。天下訩訩,但爭品位,不聞推讓,竊為聖朝恥之。
描述情況以抓住才能為清正,評價人物以實事求是罵公平,國家安危的關鍵,不可不明。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光明麵;歪曲事實是動亂滅亡的陰暗麵,不可不明察。然而人各有所長,全才很少。才有大小,成名有早晚。過去德行鄙陋,以後修身向善的人,應該受到改過自新的報答;堅守正道而不和時俗的人,應該受到為人正直的稱讚;計慮長遠而過錯微小的人,應該得到不同於一般人的評語;誠實正直而不虛假的人,應該得到廉潔忠實的稱譽;德行出眾而才能優異的人,應當受到重用。所以三位仁者殊途而同歸,四子異行卻都很合義。陳平、韓信在鄉裏被人取笑和侮辱,卻為帝王建功立業;屈原、伍子胥不為君主所容,卻名留青史,這是恰當的評論所要昭示的。
夫名狀以當才為清,品輩以得實為平,安危之要,不可不明。清平者,政化之美也;枉濫者,亂敗之惡也,不可不察。然人才異能,備體者釁。器有大小,達有早晚。前鄙後修,宜受日新之報;抱正違時,宜有質直之稱;度遠闕小,宜得殊俗之狀;任直不飾,宜得清實之譽;行寡才優,宜獲器任之用。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,四子異行而均義。陳平、韓信笑侮於邑裏,而收功於帝王;屈原、伍胥不容於人主,而顯名於竹帛,是篤論之所明也。
現在的中正,不看真才實學,專門依靠幫派利益;處事不公,專門根據個人感情。想要給的,作假以助他成名;想要讓他下的,便吹毛求疵。品級的高下隨著勢力的強弱為轉移,是非由個人的愛憎來決定。追隨世道的興衰,不顧真才實學,衰弱則降下,興盛則扶上,同一個人,十天之內就發生變化。或以賄賂使自己通達,或與計吏同行以求晉升,依托他人的人必能達到目的,恪守原則的人困窘悲傷。對己不利,必見殘害;有利於己,定要得到。所以上品官員沒有出自於貧賤之家的,下品官員沒有出身於有權勢的大族的。即或有之,亦另有原因。欺君欺世,實為亂世之源。這是九品中正製的弊病之一。
今之中正,不精才實,務依黨利,不均稱尺,備隨愛憎。所欲與者,獲虛以成譽;所欲下者,吹毛以求疵。高下逐強弱,是非由愛憎。隨世興衰,不顧才實,衰則削下,興則扶上,一人之身,旬日異狀。或以貨賂自通,或以計協登進,附托者必達,守道者困悴。無報於身,必見割奪。有私於己,必得其欲。是以上品無寒門,下品無勢族。暨時有之,皆曲有故。慢主罔時,實為亂源。損政之道一也。
設置中正,用州裏之清議,大家都服從,可以鎮住不服的,統一言論。不是說一人就能知道一州的人才,他如不知被品評者便不能被評。如此,自孔子以上,至於庖犧,都有過失,都不行,為何祇責備平常人!如果特別不善,自然可以重新選擇。現在重視他的職權而輕視其人,確立高下的等級後,回訪刁攸。他既不是州裏所歸順的,也不是職權所設置的。現在詢問他,讓正確的歸順於不服的,讓不主事的來決定事情,由此助長讒言,產生矛盾,這好像不是設立中正的本意,而是治理世俗耍深加防備的。主事者與刁攸好,刁攸降下品級又被選為二千石的,已有數人。劉良提高刁攸降下的品級,石苞懲處刁攸所幹的事,全州到處是互相論難的言論,憎惡的仇怨在大臣中結下。妻妾訴訟,給吳、楚帶來災禍;鬥雞事件,使魯國蒙受災難。於是便有人倫相爭而朋黨產生,刑獄滋生而禍根結下。這是其弊病之本著設立品級的原則,就是要使人倫有序,就像把魚串成次第排列的樣子。設立九品,把下等也列入品級,就是說才能和德行有優劣,人倫輩分有前後。現在的中正,為自己長遠打算的,則壓製一方,使無上品;淫亂卑劣下等的,則不按次序提拔,並能容納他。公家的品級變成了私人的財產。君子無怨,國家政治無懲治奸臣的措施。使得上欺明主,下亂人倫。於是使優劣和前後顛倒,把高貴和優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級以下,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麵。這是其弊病之三。
置州都者,取州裏清議,鹹所歸服,將以鎮異同,一言議。不謂一人之身,了一州之才,一人不審便坐之。若然,自仲尼以上,至於庖犧,莫不有失,則皆不堪,何獨責於中人者哉!若殊不修,自可更選。今重其任而輕其人,所立品格,還訪刁攸。攸非州裏之所歸,非職分之所置。今訪之,歸正於所不服,決事於所不職,以長讒構之源,以生乖爭之兆,似非立都之本旨,理俗之深防也。主者既善刁攸,攸之所下而複選以二千石,已有數人。劉良上攸之所下,石公罪攸之所行,駁違之論橫於州裏,嫌讎之隙結於大臣。夫桑妾之訟,禍及吳、楚;鬥雞之變,難興魯邦。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,刑獄滋生而禍根結。損政之道二也。
陛下登基,開啟天地的善心,發布廣開言路的韶令,采納忠誠的言論,遍覽天下的民情,這是太平之基,罕有之法呀。至於賞罰,自王公以至百姓,都用法來加以規定。設置中正,委以一國的重任,卻沒有賞罰的準備。人心多詐,清平的很少,所以怨恨訴訟的很多。聽任它則揭人隱私不止,禁止它則侵犯無辜沒有盡頭,辦案雖煩瑣,仍勝過侵犯無辜。現在禁止訴訟,則堵塞一國之口,培植一人勢力,使得為所欲為,無所顧忌。各被冤枉者揣著怨氣和真心話,惟獨沒蒙受到天地無私的恩惠,而長期滯留在邪佞之人的選舉之下。使得上明不下照,下情不上達。這是其弊病之四。
本立格之體,將謂人倫有序,若貫魚成次也。為九品者,取下者為格,謂才德有優劣,倫輩有首尾。今之中正,務自遠者,則抑割一國,使無上人;穢劣下比,則拔舉非次,並容其身。公以為格,坐成其私。君子無大小之怨,官政無繩奸之防。使得上欺明主,下亂人倫。乃使優劣易地,首尾倒錯。推貴異之器,使在凡品之下,負戴不肖,越在成人之首。損政之道三也。
早在聖世之時,想要改善民風,安撫百姓,就要提高鄉裏的道德,推崇六親的行為,禮教學校互相一致,這樣便與不賢有了分別。鄉老寫下他的善獻給天子,司馬根據他的能授予官職,有關部門考核業績來決定升降。所以天下人後退而自修其身,鄉裏有道德,朝廷有公正,浮華奸邪之人無處容身。現在一國之士數以千計,或流落他鄉,或在異地謀求衣食,相貌尚且不認識,談何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!不管中正知與不知,遇上應當品評之時,從官府采得美譽,從流言取得壞名。衹信自己就會被不了解所蒙蔽,聽信別人就會被彼此的局限所限製。對於認識的人僅憑愛憎,對於不認識的人僅憑關係。既不是鄉老記錄上的聲譽,又不是朝廷的考核。於是使做官的人,舍近求遠,棄本逐末。官位靠乞求而得,不由行為確定,評定品級不考核功勞,朋黨的吹捧不實。這是其弊病之五。
陛下踐阼,開天地之德,弘不諱之詔,納忠直之言,以覽天下之情,太平之基,不世之法也。然嚐罰,自王公以至於庶人,無不加法。置中正,委以一國之重,無嚐罰之防。人心多故,清平者寡,故怨訟者眾。聽之則告訐無已,禁絕則侵枉無極,與其理訟之煩,猶愈侵枉之害。今禁訟訴,則杜一國之口,培一人之勢,使得縱橫,無所顧憚。諸受枉者抱怨積直,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,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。使上明不下照,下情不上聞。損政之道四也。
一般之所以立品級看表現,是為了求人才以治民,並不是十叮羈名譽,分別好壞。孝悌本不能用於朝廷,所以家庭以外祇能講義而不能講情。已經做官,職權有大小,事情有難易,各有功報,這正是人之實用,職務之所在。現在卻相反,到了報功的期限,雖然職位很高,卻處於很低的品級,沒有政績的,卻獲得很高的品級,造就壓抑了有功勞的人而崇尚虛名。對上使朝廷的考核名存實亡,對下幫助了不務實際、拉幫結派的人。這是其弊病之六。
昔在前聖之世,欲敦風俗,鎮靜百姓,隆鄉黨之義,崇六親之行,禮教庠序以相率,賢不肖於是見矣。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,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,有司考績以明黜陟。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,州黨有德義,朝廷有公正,浮華邪佞無所容厝。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,或流徙異邦,或取給殊方,麵猶不識,況盡其才力!而中正知與不知,其當品狀,采譽於台府,納毀於流言。任己則有不識之蔽,聽受則有彼此之偏。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,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;既無鄉老紀行之譽,又非朝廷考績之課;遂使進宮之人,棄近求遠,背本逐末。位以求成,不由行立,品不校功,黨譽虛妄。損政五也。
官職的設立要針對不同的事,人的能力也不相同,發揮了他的才能則成功,失去了則失敗。現在不問才能是否合適,衹管讓他登上九品。依品級來選取人,並不是他的才能達到了;依表現又被品級所局限。如果表現符合實際情況,品級和表現仍相妨礙,就會被選舉束縛,使不得專注才能。何況今天的中正,與他疏遠的,就貶低人家的長處,與他親近的,就掩飾人家的短處。專講空話,以為虛名,則品級和能力不符,怎麼能夠處理事情。這是其弊病之七。
凡所以立品設狀者,求人才以理物也,非虛飾名譽,相為好醜。雖孝悌之行,不施朝廷,故門外之事,以義斷恩。既以在官,職有大小,事有劇易,各有功報,此人才之實效,功分之所得也。今則反之,於限當報,雖職之高,還附卑品,無績於官,而獲高敘,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。上奪天朝考績之分,下長浮華朋黨之士。損政六也。
以前為九品所頒的韶書,善惡必書,以為褒貶,當時很少有所忌諱。今天的中正,降職不明示對方錯誤,晉升不羅列對方善舉,廢棄褒貶的宗旨,僅憑感情,清濁相混,以達到個人目的。所以違反早期製度,大造聲勢,來煽動眾人,使他們都歸向自己。晉升者沒有功勞來激勵他,降職者沒有錯誤來懲戒他。獎懲不明,則風氣汙濁,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德行而專心於人情事故呢?這是其弊病之八。
凡官不同事,人不同能,得其能則成,失其能則敗。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,而以九等為例。以品取人,或非才能之所長;以狀取人,則為本品之所限。若狀得其實,猶品狀相妨,係縶選舉,使不得精於才宜。況今九品,所疏則削其長,所親則飾其短。徒結白論,以為虛譽,則品不料能,百揆何以得理,萬機何以得修?損政七也。
由此而論,立中正而沒選對人,給他權勢而無賞罰,或缺中正而無約束,所以奸邪猖狂,冤獄遍地。雖名為中正,實際是邪惡的處所;其事雖在九品,卻有八害。或在親戚中結下仇恨,或在骨肉中產生猜疑,當身陷於仇敵當中,子孫躲開禍害。逭卻是曆代的而非僅是現在的災禍。所以君主審時立法,防奸消亂,沒有不變的製度,所以周沿襲殷,有所增減。到了中正九品,古代聖賢都不用它,難道是被此事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嗎,是注重政治教化而不用它。自魏建立以來,沒見它得到人的功勞,卻帶來仇恨和不厚道的毛病。傷風敗俗,無益於教化,古今的失誤,沒有比遣更大的了。我認為應當罷免中正,廢除九品,放棄曹魏的有弊病之法,建立一代美好的製度。
前九品詔書,善惡必書,以為褒貶,當時天下,少有所忌。今之九品,所下不彰其罪,所上不列其善,廢褒貶之義,任愛憎之斷,清濁同流,以植其私。故反違前品,大其形勢,以驅動眾人,使必歸己。進者無功以表勸,退者無惡以成懲。懲勸不明,則風俗汙濁,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?損政八也。
上奏後,皇帝優韶回答他。後來司空衛罐等共同建議應廢除九品中正製,恢複古代的鄉裏議論推舉製。皇帝並沒有實行。
由此論之,選中正而非其人,授權勢而無嚐罰,或缺中正而無禁檢,故邪黨得肆,枉濫縱橫。雖職名中正,實為奸府;事名九品,而有八損。或恨結於親親,猜生於骨肉,當身困於敵讎,子孫離其殃咎。斯乃曆世之患,非徒當今之害也。是以時主觀時立法,防奸消亂,靡有常製,故周因於殷,有所損益。至於中正九品,上聖古賢皆所不為,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,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。自魏立以來,未見其得人之功,而生讎薄之累。毀風敗俗,無益於化,古今之失,莫大於此。愚臣以為宜罷中正,除九品,棄魏氏之弊法,立一代之美製。
劉毅一心為公,從早到晚,言論誠懇,不轉彎抹角,朝野都以他為榜樣。曾經在散齋期間生病,他的妻子去看他,劉毅便上奏治罪妻子解除齋戒。妻子和孩子有錯,馬上杖打,其公正如此。但因嚴厲而耿直,所以官沒做到三公。皇帝因劉毅清貧,賞錢三十萬,每Et供給米肉。七十歲時,要求退休。很久才被批準,以光祿大夫回家,門前設置攔阻人馬通行的木柵,再賞錢一百萬。
疏奏,優詔答之。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,複古鄉議裏選。帝竟不施行。
後來司徒推舉劉毅任青州大中正,尚書認為他已退休,不應再以瑣事相煩。陳留相樂安孫尹上奏說:“禮,凡位低者勞累,位尊者閑逸,這是合乎順序的。司徒魏舒、司隸校尉嚴詢和劉毅年齡相近,以前同為散騎常侍,後來各在內外任職,資曆一樣。現在嚴詢管四十萬戶州,兼督察主管百官,總掌機要,魏舒統治眾多人口,兼管中正,權衡十六州的評論,主事者不以為繁重。劉毅不過主持一州,便說他不適合以瑣碎之事相牽累,對劉毅太好,對嚴詢、魏舒太不好。如果以前聽任退休,不應又授官或升官,原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就是這樣。知人之明,即使皇帝也感到不易。尚且可再委以宰相的重任,卻不可向他谘詢人倫觀點,我私下感到不安。過去鄭武公年過八十,入朝任周司徒,雖遇退休之年,必有可用。劉毅以前為司隸校尉,執法如山,當朝大臣,多被彈劾。諺語說:‘被堯殺了,不能說堯好。’正直的大臣無派別,古今都知道。所以汲黯死於淮陽,董仲舒被削為諸侯之相。而劉毅惟獨遇到聖上,不離左右,當朝的士人都以為榮耀。劉毅雖身體局部有風病,但聰明有誌氣,一州評論並分等次,不足勞他費神。劉毅嫉惡之心稍有過頭,主事者必定懷疑他評論有損事物,所以給他很高的禮遇,不讓他幹實事,與世隔絕,使絕人倫之路。臣州裹的優秀人才祇有劉毅,越過他不用,則公正的評論就要顛倒了。”
毅夙夜在公,坐而待旦,言議切直,無所曲撓,為朝野之所式瞻。嚐散齋而疾,其妻省之,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。妻子有過,立加杖捶,其公正如此。然以峭直,故不至公輔。帝以毅清貧,賜錢三十萬,日給米肉。年七十,告老。久之,見許,以光祿大夫歸第,門施行馬,複賜錢百萬。
於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同上奏說:“謹按陳留相孫尹和我們的奏章如下。我們地處海岱之間,兼有齊、魯之風,所以人心務本而崇尚謙讓,現在雖不如過去濃厚,但遣訓仍在,所以人人崇尚德行,士人堅持操守。前些時得司徒符節,當參選州大中正。都認為光祿大夫劉毅,純孝樸素,聞名鄉裏。忠誠正直,盡力為皇帝效勞,做官不求榮譽,衹期望守住節操。修身守道,公而忘私,道德高尚,進退有節。所以能令義士仰望其風采,影響一州之風氣。他雖然年老有病,卻神清氣壯,實在是臣本州的人望。的確以劉毅的磊落風格,能做到不言而信,影響所及,各界改觀,這是一州榜樣的緣故。竊以為禮遇賢人,崇尚道德,是教化的重要內容,朝廷之任免關係到選官之路是否通暢,而士人最注重人倫。臣等無能,雖然以前沒有啟奏,現在捧著還尹的奏章,敢不啟奏。莖尹所說,不衹是愛惜對於塑隧的評論,也是全麵陳述朝廷選官的總的原則。我們認為孫尹說的當否,應當評議。”於是型塹任州中正,選舉人才,區別清濁,彈劾官吏,貶低官職,從親戚、尊貴者開始。太康六年去世,武帝摸著停屍之床震驚地說:“我失去了一位名臣,他不能生為三公!”即贈儀同三司,派人監護喪事。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說:“皇上以為劉毅鞠躬盡瘁而追封,這是聖朝認為劉毅有顯著功勳。臣謹按,謐表其德,而號表其功。現在劉毅功德並立,卻有號無謐,於義不符。以《春秋》之例來論證,謐法主要依德行而不依爵。但漠、魏相承,不是列侯,則都不計其高尚品德,不給加謐,以致位居丞相的賢臣,不如野戰的將領,碑文亦大有區別。臣願聖世奉行《春秋》古製,改革頒爵位的舊的限製,使功勞和德行的真相不相掩蓋,則沒有不服從和依靠陛下的。如果認為改革或廢除舊製,不能倉促進行,那麼劉毅的盡忠,雖不攻城掠地,但論德晉爵,亦應在列。臣膽敢思考行甫請周之例,小心地寫下劉毅的功勞和德行如上。”皇帝把奏章拿給尚書省討論,多數同意王宮的建議。奏章久壓不報。兩個兒子:劉暾、劉總。
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,尚書以毅懸車致仕,不宜勞以碎務。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:“禮,凡卑者執勞,尊得居逸,是順敘之宜也。司徒魏舒、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,往者同為散騎常侍,後分授外內之職,資途所經,出處一致。今詢管四十萬戶州,兼董司百僚,總攝機要,舒所統殷廣,兼執九品,銓十六州論議,主者不以為劇。毅但以知一州,便謂不宜累以碎事,於毅太優,詢、舒太劣。若以前聽致仕,不宜複與遷授位者,故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。夫知人則哲,惟帝難之。尚可複委以宰輔之任,不可諮以人倫之論,臣竊所未安。昔鄭武公年過八十,入為周司徒,雖過懸車之年,必有可用。毅前為司隸,直法不撓,當朝之臣,多所按劾。諺曰:‘受堯之誅,不能稱堯。’直臣無黨,古今所悉。是以汲黯死於淮陽,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。而毅獨遭聖明,不離輦轂,當世之士鹹以為榮。毅雖身偏有風疾,而誌氣聰明,一州品第,不足勞其思慮。毅疾惡之心小過,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,故高其優禮,令去事實,此為機閣毅,使絕人倫之路也。臣州茂德惟毅,越毅不用,則清談倒錯矣。”
劉暾字長升,正直有父親的遣風。太康初年罵博士,正值討論齊王司馬攸去封國,增加禮儀一事,劉暾與諸位博士因議論違背旨意被治罪。武帝大怒,收劉暾等交付廷尉。因大赦放出,免官。當初,劉暾的父親劉毅痛恨馮魷奸佞,欲奏其罪,還沒結果就去世了。現在,馮魷官運亨通,劉暾感慨道:“假如父親在世,不會讓他如此自在。”
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憑毅取正。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:“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。臣州履境海岱,而參風齊、魯,故人俗務本,而世敦德讓,今雖不充於舊,而遺訓猶存,是以人倫歸行,士識所守也。前被司徒符,當參舉州大中正。僉以光祿大夫毅,純孝至素,著在鄉閭。忠允亮直,竭於事上,仕不為榮,惟期盡節。正身率道,崇公忘私,行高義明,出處同揆。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,州閭歸其清流。雖年耆偏疾,而神明克壯,實臣州人士所思準係者矣。誠以毅之明格,能不言而信,風之所動,清濁必偃,以稱一州鹹同之望故也。竊以為禮賢尚德,教之大典,王製奪與,動為開塞,而士之所歸,人倫為大。臣等虛劣,雖言廢於前,今承尹書,敢不列啟。按尹所執,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,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。以為尹言當否,應蒙評議。”
後為酸棗令,改任侍禦史。正值司徒王渾、主簿劉輿的供詞牽連到劉暾,將被交付廷尉。王渾不想讓司徒府有遇錯,想抗拒彈劾便自己出來說。與劉暾互爭對錯,王渾發怒,退位回家。劉暾於是彈劾王渾說:“司徒王渾蒙國厚恩,位為三公,不能上佐天子,調和陰陽,下遂萬物,使卿大夫各得其所。膽敢藉劉輿抵製天子使臣,個人想要讓司徒府卷入訴訟。昔日陳平不答漢文帝之間,邴吉不問死人之變,確實合乎宰相的身份。而王渾卻發動訴訟,怨恨而退,舉動草率,無大臣之體。請免旦運官。右長史、楊丘亭侯劉肇阿諛奉迎,請大鴻臚削除其爵位封地。”凡聽說型墜奏章者無不讚美。
由是毅遂為州都,銓正人流,清濁區別,其所彈貶,自親貴者始。太康六年卒,武帝撫幾驚曰:“失吾名臣,不得生作三公!”即贈儀同三司,使者監護喪事。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:“中詔以毅忠允匪躬,贈班台司,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。臣謹按,諡者行之跡,而號者功之表。今毅功德並立,而有號無諡,於義不體。臣竊以《春秋》之事求之,諡法主於行而不係爵。然漢、魏相承,爵非列侯,則皆沒而高行,不加之諡,至使三事之賢臣,不如野戰之將。銘跡所殊,臣願聖世舉《春秋》之遠製,改列爵之舊限,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,則莫不率賴。若以革舊毀製,非所倉卒,則毅之忠益,雖不攻城略地,論德進爵,亦應在例。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,謹牒毅功行如石。”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,多同宮議。奏寢不報。二子:暾、總。
這以後武器庫著火,尚書郭彰率一百人自衛而不救火,劉暾嚴肅地責問他。郭彰發怒說:“我能裁你的角。”劉暾勃然大怒說:“你怎敢恃寵作威作福,天子法冠你想要截角嗎!”要紙筆寫奏章,郭彰伏地而不敢言,眾人勸解,才停止。郭彰長期豪華奢侈,每次外出後麵都跟著百餘人。從此以後,務求儉樸。
暾字長升,正直有父風。太康初為博士,會議齊王攸之國,加崇典禮,暾與諸博士坐議迕旨。武帝大怒,收暾等付廷尉。會赦得出,免官。初,暾父毅疾馮紞奸佞,欲奏其罪,未果而卒。至是,紞位宦日隆,暾慨然曰:“使先人在,不令紞得無患。”
劉暾升任太原內史,趙王司馬倫篡位後,使之假征虜將軍,不肯接受,與三王共同起義。惠帝複位,劉暾為左丞,正色立朝,三省清正肅穆。不久,兼任禦史中丞,上奏免尚書仆射、束安公司馬繇及王粹、董艾等十餘人官。朝廷表揚他,於是正式任命。升任中庶子、左衛將軍、司隸校尉,上奏免武陵王司馬澹及何綏、劉坦、溫畿、李晅等人官。長沙王司馬義討伐齊王司馬同,劉暾參預謀劃,封朱虛縣公,給封戶一千八百戶。司馬義死,免官。不久,再為司隸校尉。
後為酸棗令,轉侍禦史。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,將收付廷尉。渾不欲使府有過,欲距劾自舉之。與暾更相曲直,渾怒,便遜位還第。暾乃奏渾曰:“謹按司徒王渾,蒙國厚恩,備位鼎司,不能上佐天子,調和陰陽,下遂萬物之宜,使卿大夫各得其所。敢因劉輿拒扞詔使,私欲大府興長獄訟。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,邴吉不問死人之變,誠得宰相之體也。既興刑獄,怨懟而退,舉動輕速,無大臣之節,請免渾官。右長史、楊丘亭侯劉肇,便辟善柔,苟於阿順,請大鴻臚削爵土。”諸聞暾此奏者,皆歎美之。
惠帝到長安時,留劉暾守洛陽。河間王司馬顒派人要鴆殺羊皇後,劉暾便與留台仆射荀藩、河南尹周馥等上表,說皇後無罪。奏章在《後傳》。司馬題見表,大怒,派陳顏、呂朗率騎兵五千捉劉暾,劉暾東奔高密王司馬略。正值劉根叛亂,司馬略以劉暾為大都督,加鎮軍將軍討伐劉根。劉根失利,回洛陽。到酸棗,值東海王司馬越奉迎皇帝。等皇帝回洛陽,羊皇後也回皇宮。皇後派使臣感謝劉墜說:“靠劉司隸的忠誠才有今天。”以舊勳再次封爵,加光祿大夫。
其後武庫火,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,暾正色詰之。彰怒曰:“我能截君角也。”暾勃然謂彰曰:“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,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!”求紙筆奏之,彰伏不敢言,眾人解釋,乃止。彰久貴豪侈,每出輒眾百餘人。自此之後,務從簡素。
劉暾妻已死,先埋入陪葬地。兒子更生剛結婚,依家法,兒媳應當拜墓,全家帶著敷十乘車的賓客親屬,還有酒食前去。以前,洛陽令王棱被司馬越信任,輕視劉暾,劉暾總想治他,他恨劉暾。當時劉聰、王彌駐紮在河北,京城危險恐懼。王棱告訴司馬越,說劉暾輿王彌是同鄉,想要投奔他。司馬越急令騎兵追劉暾,右長史傅宣說劉暾不會這樣。劉暾聽說後,沒到墓地而返回,以此行的目的責問司馬越,司馬越很慚愧。
暾遷太原內史,趙王倫篡位,假征虜將軍,不受,與三王共舉義。惠帝複阼,暾為左丞,正色立朝,三台清肅。尋兼禦史中丞,奏免尚書仆射、東安公繇及王粹、董艾等十餘人。朝廷嘉之,遂即真。遷中庶子、左衛將軍、司隸校尉,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、劉坦、溫畿、李晅等。長沙王乂討齊王冏,暾豫謀,封硃虛縣公,千八百戶。乂死,坐免。頃之,複為司隸。
等劉曜侵犯京城,以劉暾為撫軍將軍、假節、都督守城諸軍事。劉曜撤退,升任尚書仆射。司馬越害怕劉暾久居監察部門。又為眾望所歸,於是以之為右光祿大夫,領太子少傅,加散騎常侍。表麵上是晉升,實際奪了他的權。懷帝又令劉暾領衛尉,加特進。後來再以劉暾為司隸校尉,加侍中。劉暾五次任司隸校尉,這是因為人事和洽。
及惠帝之幸長安也,留暾守洛陽。河間王顒遣使鴆羊皇後,暾乃與留台仆射荀籓、河南尹周馥等上表,理後無罪。語在《後傳》。顒見表,大怒,遣陳顏、呂朗率騎五千收暾,暾東奔高密王略。會劉根作逆,略以暾為大都督,加鎮軍將軍討根。暾戰失利,還洛。至酸棗,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。及帝還洛,羊後反宮。後遣使謝暾曰:“賴劉司隸忠誠之誌,得有今日。”以舊勳複封爵,加光祿大夫。
王彌到洛陽,百官被殺。王彌認為劉暾是鄉裏老成望重的人,所以沒有加害他。劉暾乘機對王彌說:“當今英雄逐鹿,國家分裂,有奇功者被人不容。將軍自發兵以來,攻無不克,戰無不勝,卻與劉曜不和,應當想想文種的災禍,以範蠡為師。況且將軍怎能無稱王之意,東王本州。以觀形勢,上可以統一天下,下可以成鼎立之事,做個劉備或孫權!按蒯通諫劉邦的話,將軍應早作打算。”王彌認為有理,派劉暾到青州,與曹嶷謀劃,且任用他。劉暾到柬阿,被石勒巡邏騎兵抓獲,見王彌給曹嶷的信大怒,於是殺了他。劉暾有兩個兒子:劉佑、劉白。
暾妻前卒,先陪陵葬。子更生初婚,家法,婦當拜墓,攜賓客親屬數十乘,載酒食而行。先是,洛陽令王棱為越所信,而輕暾,暾每欲繩之,棱以為怨。時劉聰、王彌屯河北,京邑危懼。棱告越,雲暾與彌鄉親而欲投之。越嚴騎將追暾,右長史傅宣明暾不然。暾聞之,未至墓而反,以正義責越,越甚慚。
劉佑為太傅屬,任太子舍人。劉皇剛直有才幹,東海王司馬越恨他,私自派上軍魚儉率一百餘人到劉暾家,搶劫財物,殺了型皇離去。
及劉曜寇京師,以暾為撫軍將軍、假節、都督城守諸軍事。曜退,遷尚書仆射。越憚暾久居監司,又為眾情所歸,乃以為右光祿大夫,領太子少傅,加散騎常侍。外示崇進,實奪其權。懷帝又詔暾領衛尉,加特進。後複以暾為司隸,加侍中。暾五為司隸,允協物情故也。
劉總字弘紀,好學,正直忠實,過繼給叔父型彪,官至北軍中候。
王彌入洛,百官殲焉。彌以暾鄉裏宿望,故免於難。暾因說彌曰:“今英雄競起,九州幅裂,有不世之功者,宇內不容。將軍自興兵已來,何攻不克,何戰不勝,而複與劉曜不協,宜思文種之禍,以範蠡為師。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,東王本州,以觀時勢,上可以混一天下,下可以成鼎峙之事,豈失孫、劉乎!蒯通有言,將軍宜圖之。”彌以為然,使暾於青州,與曹嶷謀,且征之。暾至東阿,為石勒遊騎所獲,見彌與嶷書而大怒,乃殺之。暾有二子:佑、白。
程衛字長玄,是廣平曲周人。年少就建立操守品行,剛正嚴肅。劉毅聞其名,征用為都官從事。劉毅上奏中護軍羊琇違法應死。武帝與琇以前有交情,於是派齊王司馬攸去說情,劉毅答應了。劉毅堅持以為不可,直接駕車到護軍營中,拿下圭瑟屬官,拷問隱情,先奏芏透的不檢行為,然後報告劉毅。由此名震遐邇,百官嚴肅行事。於是征用為公府掾,升任尚書郎、侍禦史,在職都以辦事幹練聞名。補洛陽令,曆任安定、頓丘太守,所到之處,成績顯著。在任上去世。
佑為太傅屬,白太子舍人。白果烈有才用,東海王越忌之,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暾第,為劫取財物,殺白而去。
和崤字長輿,是汝南西平人。祖父和洽,毯時任尚書令。父親和迪,魏時任吏部尚書。和墮年少有風度,羨慕舅舅夏侯玄的為人,自重,有盛名於當時。朝野稱讚他能整治風俗,理順人倫。繼承父親的爵位上蔡伯,開始做官為太子舍人。多次升任穎川太守,為政清平簡約,很得百姓歡心。太傅從事中郎庾頡見到他感歎道:“和墮高聳如千丈鬆,雖多節,用於大廈,是棟梁之材。”買童亦看重他,在亙遊麵前稱讚他,召入任給事黃門侍郎,升任中書令,武帝很器重他。過去監和令同車入朝,當時苟勖任監,和崤鄙視他的為人,盛氣淩人,.每次入朝,和崤獨坐一車。監、令不同車,自和崤開始。
總字弘紀,好學直亮,後叔父彪,位至北軍中候。
吳平定,以參與謀劃之功,賜弟弟和鬱爵汝南亭侯。嶠改任侍中,愈被信任厚待,與任愷、張華親密。嶠見太子不聽命令,在旁邊座位上說:“皇太子有淳樸之風,而衰世多虛偽,恐怕不明白陛下家事。”武帝沉默不答。後來輿荀顗、荀勖共同侍候,帝說:“太子最近入朝,稍有長進,你們可一起去,大概講講人世間事。”完畢而歸,荀顗、荀勖共同稱讚太子聰明高雅,的確如皇帝所說。和崤說:“氣質如初啊!”皇帝不高興地站起來。扣崤回到家裹,常常感慨,知道不被用,仍不能自己。在皇帝處談到國家,總替太子擔憂。皇帝知道他言辭忠誠,每次不以文字相酬答。後輿歪’嶇說話,不再提到將來。有人告訴賈妃,妃恨他。太康末年,任尚書,以母親的喪事離職。
程衛,字長玄,廣平曲周人也。少立操行,強正方嚴。劉毅聞其名,辟為都官從事。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。武帝與琇有舊,乃遣齊王攸喻毅,毅許之。衛正色以為不可,徑自馳車入護軍營,收琇屬吏,考問陰私,先奏琇所犯狼藉,然後言於毅。由是名振遐邇,百官厲行。遂辟公府掾,遷尚事郎、侍禦史,在職皆以事幹顯。補洛陽令,曆安定、頓丘太守,所蒞著績。卒於官。
等到惠帝即位,拜任太子少傅,加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。太子拜見太後,和嬌跟入。賈後讓惠帝問和崤:“你以前說我不明白家事,今天你定要說什麼?”和崤說:“臣以前侍奉皇帝,曾有此話。話不奏效,是國家的福氣。臣敢逃過此罪嗎!”元康二年去世,追封金紫光祿大夫,加金章紫綬,官位如前。謐號簡。和崤家產豐富,可與王比,但吝嗇,以此被人譏笑,杜預認為和崤有錢癖。以弟弟和鬱的兒子和濟繼嗣,位至中書郎。
和嶠,字長輿,汝南西平人也。祖洽,魏尚書令。父逌,魏吏部尚書。嶠少有風格,慕舅夏侯玄之為人,厚自崇重。有盛名於世,朝野許其能風俗,理人倫。襲父爵上蔡伯,起家太子舍人。累遷潁川太守,為政清簡,甚得百姓歡心。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:“嶠森森如千丈鬆,雖磥可多節目,施之大廈,有棟梁之用。”賈充亦重之,稱於武帝,入為給事黃門侍郎,遷中書令,帝深器遇之。舊監令共車入朝,時荀勖為監,嶠鄙勖為人,以意氣加之,每同乘,高抗專車而坐。乃使監令異車,自嶠始也。
和鬱字仲輿,才幹和名望趕不上和崤,卻以清正幹練聞名,曆任尚書左右仆射、中書令、尚書令。盜陽陷落後,投靠苞墮,因病去世。
吳平,以參謀議功,賜弟鬱爵汝南亭侯。嶠轉侍中,愈被親禮,與任愷、張華相善。嶠見太子不令,因侍坐曰:“皇太子有淳古之風,而季世多偽,恐不了陛下家事。”帝默然不答。後與荀顗、荀勖同侍,帝曰:“太子近入朝,差長進,卿可俱詣之,粗及世事。”即奉詔而還。顗、勖並稱太子明識弘雅,誠如明詔。嶠曰:“聖質如初耳!”帝不悅而起。嶠退居,恆懷慨歎,知不見用,猶不能已。在禦坐言及社稷,未嚐不以儲君為憂。帝知其言忠,每不酬和。後與嶠語,不及來事。或以告賈妃,妃銜之。太康末,為尚書,以母憂去職。
武陔字元夏,是沛國竹邑人。父親武周,魏時任衛尉。武陔深沉敏銳有度量,早有聲譽,與二弟武韶字叔夏、武茂字季夏孩童時就知名,即使父輩兄弟和鄉裏老成而有名望的人,也都分辨不出他們的優劣。同郡劉公榮能鑒賞人物,常到武周家,武周讓三個兒子出來見麵。公榮說:“都是國士。元夏最優,有王佐之才,施展才力去做官,可為司徒。叔夏、季夏不次於常伯、納。
及惠帝即位,拜太子少傅,加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。太子朝西宮,嶠從入。賈後使帝問嶠曰:“卿昔謂我不了家事,今日定雲何?”嶠曰:“臣昔事先帝,曾有斯言。言之不效,國之福也。臣敢逃其罪乎!”元康二年卒,贈金紫光祿大夫,加金章紫綬,本位如前。永平初,策諡曰簡。嶠家產豐富,擬於王者,然性至吝,以是獲譏於世,杜預以為嶠有錢癖。以弟鬱子濟嗣,位至中書郎。
武陔年少時喜歡品評人物,與穎川太守陳泰友善。魏明帝時,升任下邳太守。景帝為大將軍,引為從事中郎,多次升至司隸校尉,改任太仆卿。先封為亭侯,立五等爵位時,改封薛縣侯。文帝很器重他,多次與他評論當時人物。曾問陳泰和他的父親陳群哪個更優。武陔各說他們的長處,認為陳群、陳泰差不多,文帝同意。
鬱字仲輿,才望不及嶠,而以清幹稱,曆尚書左右仆射、中書令、尚書令。洛陽傾沒,奔於苟晞,疾卒。
泰始初年,拜任尚書,掌管吏部,升任左仆射、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武陔以年老是舊臣,名聲和官位都很高,自認為無輔佐之功,又在魏已為大臣,不得已而做官,很想辭職,保全節操,當世以為美談。在任上去世,謐號定。兒子武輔繼嗣。
武陔,字元夏,沛國竹邑人也。父周,魏衛尉。陔沈敏有器量,早獲時譽,與二弟韶叔夏、茂季夏並總角知名,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,莫能覺其優劣。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,常造周,周見其三子焉。公榮曰:“皆國士也。元夏最優,有輔佐之才,陳力就列,可為亞公。叔夏、季夏不減常伯、納言也。”
武韶曆任吏部郎、太子右衛率、散騎常侍。亙遞以品德和操行著稱,名聲次於亙瞪,任上洛太守、散騎常侍、侍中、尚書。穎川荀愷比武茂小,是武帝姑姑的兒子,自恃是貴戚,想與武茂結交,武茂不肯,由此結怨。等到楊駿被殺,荀愷當時任仆射,因武茂是楊駿的表兄弟,誣為叛黨,於是被害。武茂清廉正直,聞名朝野,一旦含冤而死,天下痛心。侍中傅祗上奏為他申辯,後來追封為光祿勳。
陔少好人倫,與潁川陳泰友善。魏明帝世,累遷下邳太守。景帝為大將軍,引為從事中郎,累遷司隸校尉,轉太仆卿。初封亭侯,五等建,改封薛縣侯。文帝甚親重之,數與詮論時人。嚐問陳泰孰若其父群,陔各稱其所長,以為群、泰略無優劣,帝然之。泰始初,拜尚書,掌吏部,遷左仆射、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陔以宿齒舊臣,名位隆重,自以無佐命之功,又在魏已為大臣,不得已而居位,深懷遜讓,終始全潔,當世以為美談。卒於位,諡曰定。子輔嗣。
任愷字元褒,是樂安博昌人。父親任昊,魏時任太常。任愷年少有見識和度量,娶魏明帝的女兒,多次升任中書侍郎、員外散騎常侍。晉國建立,任侍中,封昌國縣侯。
韶曆吏部郎、太子右衛率、散騎常侍。
任愷有治國的才幹,大小事情都管。為人忠正,以國家屬己任,皇帝器重而親近他,政事多向他谘詢。泰始初年,鄭衝、王祥、何曾、荀顥、裴秀等各以老、病回家。皇帝優待寵信他們,不想勞其筋骨,多次派任愷告訴他們旨意,谘詢當朝大事,參與議論得失。任愷討厭賈充的為人,不想讓他久執朝政,總壓製他。賈充恨他,卻拿他沒辦法。後趁空說任愷忠貞正直,宜在束宮,使照顧太子。皇帝同意,以為太子少傅,侍中照舊,賈充的陰謀未得逞。正值秦、雍賊寇騷擾,天子擔憂。任愷乘機說:“秦、涼覆沒,關右騷動,這的確值得國家深思。應迅速鎮守安撫,使人心穩定。如果不是有威望、有計謀的重臣,無以收複西土。”皇帝問:“誰可擔當此任?”任愷說:“買充可以。”中書令庾純亦說是,於是韶令賈充西鎮長安。賈充用萄勖的計謀得以留下來。
茂以德素稱,名亞於陔,為上洛太守、散騎常侍、侍中、尚書。潁川荀愷年少於茂,即武帝姑子,自負貴戚,欲與茂交,距而不答,由是致怨。及楊駿誅,愷時為仆射,以茂駿之姨弟,陷為逆黨,遂見害。茂清正方直,聞於朝野,一旦枉酷,天下傷焉。侍中傅祗上申明之,後追贈光祿勳。
買充既然被皇帝所器重,就想控製權勢,而庾純、張華、溫顯、向秀、和崤等都和任愷友好,楊珧、王恂、華廳等都和買充親近,於是朋黨相爭。皇帝知道後,在式幹殿宴請賈充、任愷,對賈充等說:“朝廷應當統一,大臣應當和睦。”賈充、任愷對拜道歉作罷。接著賈充、任愷等因為皇帝已經知道而不責備,結怨越來越深,外表上互相推祟,內心卻很不平衡。有人給賈充出主意說:“任愷總管門下機要,得與皇帝親近,應啟奏皇帝令他主持選舉,便能漸漸疏遠,造就是一個都令史的事情。何況九品人物難弄清,有機可乘。”買充於是稱讚任愷有才能,應當主持選舉。皇帝沒起疑心,還說買充推薦了合適人選。第二天就以任愷為吏部尚書,加奉車都尉。
任愷,字元褒,樂安博昌人也。父昊,魏太常。愷少有識量,尚魏明帝女,累遷中書侍郎、員外散騎常侍。晉國建,為侍中,封昌國縣侯。
任愷在尚書任上,選舉公平,盡心盡力,但見皇帝少了。賈充與荀勖、馮魷乘機進讒言,說任愷奢侈,用皇帝的餐具。買充讓尚書右仆射、高陽王司馬珪彈劾任愷,於是免官。有關部門逮捕太官宰人檢查核實,結果是任愷的妻子齊長公主得到的用作賞賜的魏時的皇帝用品。任愷已被免了官,而誹謗卻越來越多,皇帝漸漸疏遠了他。但山濤明白任愷為人曠達機敏有才智,推舉為河南尹。因治賊無功,又被免官。再次升任光祿勳。
愷有經國之幹,萬機大小多管綜之。性忠正,以社稷為己任,帝器而昵之,政事多諮焉。泰始初,鄭衝、王祥、何曾、荀顗、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。帝優寵大臣,不欲勞以筋力,數遣愷諭旨於諸公,諮以當世大政,參議得失。愷惡賈充之為人也,不欲令久執朝政,每裁抑焉。充病之,不知所為。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,宜在東宮,使護太子。帝從之,以為太子少傅,而侍中如故,充計畫不行。會秦、雍寇擾,天子以為憂。愷因曰:“秦、涼覆敗,關右騷動,此誠國家之所深慮。宜速鎮撫,使人心有庇。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,無以康西土也。”帝曰:“誰可任者?”愷曰:“賈充其人也。”中書令庾純亦言之,於是詔充西鎮長安。充用荀勖計得留。
任愷向來能鑒賞人物,加上對公事盡力、謹慎,很得朝野稱讚。但賈充朋黨又暗示有關部門彈劾任愷與立進令劉友勾結。事下尚書,任愷不服。尚書杜友、廷尉劉良都是忠於職守的人,知道任愷被買充壓製,想要替他申辯,所以遲遲不判,於是任愷和杜友、劉良都免官。任愷既然丟了官,便縱酒享樂,嚐盡滋味以保養自己。當初,何劭認為公子奢侈,每次進食必定湊齊四方佳肴,任愷更過分,一餐萬金,還說沒有可吃之萊。任愷有時去朝見,皇帝又慰問他,他開始不回答,衹是哭。後啟用為太仆,改任太常。
充既為帝所遇,欲專名勢,而庾純、張華、溫顒、向秀、和嶠之徒皆與愷善,楊珧、王恂、、華暠等充所親敬,於是朋黨紛然。帝知之,召充、愷宴於式乾殿,而謂充等曰:“朝廷宜一,大臣當和。”充、愷各拜謝而罷。既而充、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,結怨愈深,外相崇重,內甚不平。或為充謀曰:“愷總門下樞耍,得與上親接,宜啟令典選,便得漸疏,此一都令史事耳。且九流難精,間隙易乘。”充因稱愷才能,宜在官人之職。帝不之疑,謂充舉得其才。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,加奉車都尉。
當初,魏舒雖曆任郡守,但未被器重,任愷為侍中,推薦魏舒為散騎常侍。至此魏舒為右光祿、開府,領司徒,皇帝走到殿前讓任愷授官。魏舒雖以寬宏大量著稱,當時人卻認為任愷有輔佐之才,而魏舒位至三公,任愷衹是有名無實的九卿,莫不為之憤慨。任愷不得誌,最後因憂慮去世,終年六十一歲,謐號元,兒子任罕繼嗣。
愷既在尚書,選舉公平,盡心所職,然侍覲轉希。充與荀勖、馮紞承間浸潤,謂愷豪侈,用禦食器。充遣尚書右仆射、高陽王珪奏愷,遂免官。有司收太官宰人檢核,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禦器也。愷既免而毀謗益至,帝漸薄之。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,舉為河南尹。坐賊發不獲,又免官。複遷光祿勳。
任罕字王儉,年幼有家風,才能和名望不如任愷,以善良之舉獲得聲譽,是清正公平的優秀士人。曆任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、兗州刺史、大鴻臚。
愷素有識鑒,加以在公勤恪,甚得朝野稱譽。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。事下尚書,愷對不伏。尚書杜友、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,知愷為充所抑,欲申理之,故遲留而未斷,以是愷及友、良皆免官。愷既失職,乃縱酒耽樂,極滋味以自奉養。初,何劭以公子奢侈,每食必盡四方珍饌,愷乃逾之,一食萬錢,猶雲無可下箸處。愷時因朝請,帝或慰諭之,愷初無複言,惟泣而已。後起為太仆,轉太常。
崔洪字良伯,是博陵安平人。高祖崔宮,在漢代很著名。父親崔讚,魏時任吏部尚書、左仆射,以雅量著稱。崔洪年少時以清正嚴肅出名,耿直遇人,人有過錯,就當麵批評,過後沒有二話。
初,魏舒雖曆位郡守,而未被任遇,愷為侍中,薦舒為散騎常侍。至是舒為右光祿、開府,領司徒,帝臨軒使愷拜授。舒雖以弘量寬簡為稱,時以愷有佐世器局,而舒登三公,愷止守散卿,莫不為之憤歎也。愷不得誌,竟以憂卒,時年六十一,諡曰元,子罕嗣。
武帝朝,為禦史治書。當時長樂馮恢的父親為弘農太守,愛小兒子馮淑,想把爵位傳給他。馮恢的父親去世,馮恢服喪期滿,便回鄉裏,用草編織成簡陋的房屋,假裝成啞巴,馮淑得以繼承。馮恢開始做官為博士祭酒,散騎常侍翟嬰推薦馮恢,說他有高尚的操行,超凡脫俗,有古烈士之風。崔洪上奏說馮恢不能帶頭履行儒者的品德操行,令學生在左右輪流值班,雖有讓侯的小善,卻不能說蓋世無雙,翟嬰是華而不實之流。於是免翟嬰的官,朝廷害怕他。不久任尚書左丞,當時人評價他說:“叢生荊棘,來自博陵。在南為鷂,在北為鷹。”
罕字子倫,幼有門風,才望不及愷,以淑行致稱,為清平佳士。曆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、兗州刺史、大鴻臚。
任吏部尚書,選官公平,沒有私下求情的。推薦雍州刺史卻說代替自己任左丞。邵說後來檢舉崔洪,崔洪對人說:“我推舉邵丞而他反而彈劾我,這是挽弓射自己。”邵說聽說後說:“過去趙宣子以韓厥為司馬,韓厥卻以軍法殺了宣子的仆人。宣子對各位大夫說:‘可以祝賀我了,我選韓厥是要讓他盡責任的。崔侯為國選才,我以才被選,衹以官職為重,都表現得很公正,為什麼要說這麼不公道的話!”崔洪聽說後很看重他。
崔洪,字良伯,博陵安平人也。高祖寔,著名漢代。父讚,魏吏部尚書、左仆射,以雅量見稱。洪少以清厲顯名,骨鯁不同於物,人之有過,輒麵折之,而退無後言。武帝世,為禦史治書。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,愛少子淑,欲以爵傳之。恢父終,服闋,乃還鄉裏,結草為廬,陽喑不能言,淑得襲爵。恢始仕為博士祭酒,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,侔繼古烈。洪奏恢不敦儒素,令學生番直左右,雖有讓侯微善,不得稱無倫輩,嬰為浮華之目。遂免嬰官,朝廷憚之。尋為尚書左丞,時人為之語曰:“叢生棘刺,來自博陵。在南為鷂,在北為鷹。”選吏部尚書,舉用甄明,門無私謁。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為左丞。詵後糾洪,洪謂人曰:“我舉郤丞而還奏我,是挽弩自射也。”詵聞曰:“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,以軍法戮宣子之仆。宣子謂諸大夫曰:‘可賀我矣,我選厥也任其事。’崔侯為國舉才,我以才見舉,惟官是視,各明至公,何故私言乃至此!”洪聞其言而重之。
崔洪口不言財物,手不握珠玉。汝南王司馬亮常宴請大臣,以琉璃鍾行酒。酒到崔洪處,他不拿。司馬亮問原因,回答:“想到握玉不能快走的緣故。”但的確違背常理,所以是詭辯。楊駿被殺,崔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近,因牽連坐罪被黜落。後為大司農,在任上去世。兒子崔廓,散騎侍郎,亦以正直聞名。
洪口不言貨財,手不執珠玉。汝南王亮常晏公卿,以琉璃鍾行酒。酒及洪,洪不執。亮問其故,對曰:“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”。然實乖其常性,故為詭說。楊駿誅,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,坐見黜。後為大司農,卒於官。子廓,散騎侍郎,亦以正直稱。
郭奕字大業,是太原陽曲人。年少有大名,山濤稱讚他高超不凡有雅量。最初任野王令,羊枯常路過,郭奕感歎道:“羊叔子何必次於郭大業!”沒多久又去,郭奕又感歎道:“羊叔子不是凡人啊。”於是送羊祜出界敷百裏,被治罪免官。鹹熙末年,為文帝相國主簿。這時鍾會在蜀反叛,荀勖是鍾會的侄甥,小時候在鍾會家長大,荀勖為文帝掾,郭奕啟奏免他的官,文帝雖不聽,但知道他公正。
郭奕,字大業,太原陽曲人也。少有重名,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。初為野王令,羊祜常過之,奕歎曰:“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!”少選複往,又歎曰:“羊叔子去人遠矣。”遂送祜出界數百裏,坐此免官。鹹熙末,為文帝相國主薄。時鍾會反於蜀,荀勖即會之從甥,少長會家,勖為文帝掾,奕啟出之。帝雖不用,然知其雅正。武帝踐阼,初建東宮,以奕及鄭默並為中庶子。遷右衛率、驍騎將軍,封平陵男。鹹寧初,遷雍州刺史、鷹揚將軍,尋假赤幢曲蓋、鼓吹。奕有寡姊,隨奕之官,姊下僮仆多有奸犯,而為人所糾。奕省按畢,曰:“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?”遂遣而不問。時亭長李含有俊才,而門寒為豪族所排,奕用為別駕,含後果有名位,時以奕為知人。
武帝即位,初建東宮,以郭奕和鄭默為中庶子。升任右衛率、驍騎將軍,封平陵男。鹹寧初年,升任雍州刺史、鷹揚將軍,不久借給他赤幢曲蓋、鼓吹。郭奕有個寡婦姐姐,隨郭奕去做官,她手下的奴仆有許多犯罪的,於是被人檢舉。郭奕審查完畢,說:“大丈夫豈能以老姐姐求名?”於是送走不問。當時亭長李含有俊才,但門第低微被大族排擠,郭奕用為別駕,李含後來果然做了大官,當時人認為郭奕能識別人物。
太康中,征為尚書。奕有重名,當世朝臣皆出其下。時帝委任楊駿,奕表駿小器,不可任以社稷。帝不聽,駿後果誅。及奕疾病,詔賜錢二十萬,日給酒米。太康八年卒,太常上諡為景。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,諡與景皇同,不可,請諡曰穆。詔曰:“諡所以旌德表行,按諡法一德不懈為簡。奕忠毅清直,立德不渝。”於是遂賜諡曰簡。
太康年間,征用為尚書。郭奕有大名聲,當朝大臣都排在他下麵。當時武帝委任楊駿,郭奕說楊駿度量小,不可委以國家重任。武帝不聽,楊駿後來果然被殺。等到郭奕病重,韶令賞錢二十萬,每天給酒米。太康八年去世,太常上謐號景。有關部門認為貴賤不同號,謐號與景皇同,不可,請求為穆。韶書說:“謐號所以表彰德行,按謐法固守道德不鬆懈為簡。郭奕忠誠剛毅,廉潔正直,守德不渝。”於是賜謐號簡。
侯史光,字孝明,東萊掖人也。幼有才悟,受學於同縣劉夏。舉孝廉,州辟別駕。鹹熙初,為洛陽典農中郎將,封關中侯。泰始初,拜散騎常侍,尋兼侍中。與皇甫陶、荀暠持節循省風俗,及還,奏事稱旨,轉城門校尉,進爵臨海侯。其年詔曰:“光忠亮篤素,有居正執義之心,曆職內外,恪勤在公,其以光為禦史中丞。雖屈其